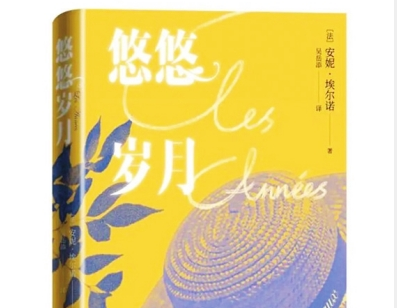狗是通人性的。在川西北的鄉壩頭,家家戶戶養狗看家護院,它們都是當之無愧的“守門神”。
我家從前養過一條狗,渾身毛色黃得像曬透的苞谷,油亮油亮的。我們都喊它老黃——這個名字,一叫就是好些年。
那是個寒風刺骨的冬日黃昏,母親從莊稼地往家走,田坎邊的風“嗚嗚”地刮著。老黃不知何時跟在了她身后,不緊不慢地晃悠著。母親咋個攆、咋個吆喝,它都像塊嚼不爛的口香糖,硬是黏著回了家。農村老話講“豬來窮,狗來富”,或許為了圖個吉利,又或許是老黃濕漉漉的眼神,母親動了惻隱之心。
老黃不挑食,好養活。沒兩年光景,就長成了威風凜凜的大狗。一身黃毛在太陽底下泛著光,身長腿長,耳朵總是警覺地支棱著,見了生人就“汪汪汪”叫個不停。鄰居家的小娃娃們遠遠瞧見它,都嚇得繞道走,它也因此沒少挨罵挨打,可性子還是倔得很。
都說“狗拿耗子多管閑事”,老黃還真管過一樁“閑事”,硬生生把兩家二十年不相往來的恩怨給化解了。那時候我和哥哥在三十多里外的區公所讀書,沒親眼瞧見,但聽母親講過無數回。那些年大家都窮,為了包產地的溝溝坎坎、房前屋后巴掌大的地方,鄰里間爭嘴打架是常有的事。
那天,隔壁張嬸到河溝邊洗衣裳。臘月的風刀子似的刮著,她彎腰去撈被水沖走的衣裳,冷不丁腳底一滑,“撲通”栽進了河溝。河溝早被鄉親們掏得淤泥見底,岸邊連根抓扶的枝條都沒有,張嬸穿得厚、身子胖,越撲騰越往下沉,只能拼命喊“救命”!
“汪,汪,汪——”老黃的叫聲突然劃破寂靜。它正巧路過河溝,瞧見有人在水里掙扎,它撒腿就往王嬸家跑。王嬸被吵得心煩,抄起棍棒就去攆,可老黃挨了好幾下也不躲,反而叼住她的褲腳直往河邊拽。王嬸這才覺著不對勁,叫上丈夫跟著老黃跑到河邊,一眼就看見在水里撲騰的張嬸。王嬸丈夫二話不說跳進刺骨的河水里,王嬸趕忙遞上手里的棍棒,七手八腳把張嬸拉上了岸。張嬸凍得嘴唇烏青、牙齒打顫,王嬸又抱來谷草生火給她取暖。打那以后,兩家的心結解開了,再沒為雞毛蒜皮的小事紅過臉。
這么多年過去,我為啥總記著老黃?因為它曾悄無聲息地失蹤過整整一周,而這事,還和我與哥哥有關。
那時哥哥讀高二,我讀初一,每個周日吃過晌午飯,就得背著裝滿米、紅苕和泡菜罐的背篼,走三十里山路去區中學。老黃總愛跟在后頭,往常送到卡房埡——那個和隔壁鄉鎮交界的地方,它才會慢悠悠往回走。
可那天,我和哥哥邊走邊擺龍門陣,等走了很遠才發現,老黃還在身后跟著!我們慌了神,又是吆喝又是扔石子,把它攆走,可它還是跟上來了。
我剛進校門,老黃搖著尾巴,眼巴巴地望著我,喉嚨里還發出“嗚嗚”的委屈聲。哥哥跑遍校園,只尋來幾根快爛的紅苕和一點剩飯。老黃狼吞虎咽吃完,我們又開始攆它。它一步三回頭,走幾步就停下來看看,生怕被拋棄。想起平日里它的好——父母喊一聲“老黃,去把大鵝吆回來”,它立馬撒腿就跑;曬糧食時,不用吩咐就守在旁邊攆麻雀;家里來了客人,只要說一聲“莫亂叫”,它就乖乖趴在一旁不吭聲……
我們把老黃攆到旦家廟,預習課的鈴聲就響了。
那時候每周要讀六天書,周五下午一放學,我和哥哥就急急忙忙往家趕。到家后,沒瞧見老黃撲上來撒歡。“黃狗呢?”我們問。母親愣了一下:“不是跟你們走了嗎?我們還以為在學校呢。”
老黃真的丟了。整整六天,音信全無。我和哥哥坐在門檻上,心里七上八下:是不是被人拴住了?是不是遇到壞人遭了毒手?是不是迷路了還在荒野里挨餓……那晚,我翻來覆去睡不著,滿腦子都是老黃的影子。
半夜里,“噠噠噠”,一陣抓門聲從父母的房門上傳來。母親趕忙拉亮電燈,披著衣服沖出去,緊接著傳來她驚喜的喊聲:“老黃回來了!老黃回來了!”我和哥哥光著腳就往外跑,燈光下的老黃瘦得只剩一把骨頭,雜亂的皮毛上沾滿泥漬,左后腿一瘸一拐,連叫聲都微弱得聽不清,可眼睛里卻閃著光,像是有千言萬語要訴說。母親轉身就往廚房跑,煮了滿滿一碗面,還放了好大一塊豬油——那可是我們平日里都舍不得吃的好東西。
我和哥哥蹲在老黃身邊,眼淚“吧嗒吧嗒”往下掉。真不敢想,這六天它到底經歷了啥,走了多少冤枉路,又挨了多少餓。
后來我去了更遠的地方讀書,每年寒暑假才能回家。和老黃相處的日子越來越少,可每次推開家門,總盼著那個熟悉的影子搖著尾巴沖出來。再后來,哥哥在信里說,老黃是老死的,父母把它埋在了屋后的竹林里。
從那以后,我們家再沒養過狗。日子一天天過去,屋后的竹林依舊沙沙作響,再也沒有一只狗,會追著我們的腳步,伴隨我們走三十里山路了。(齊述洋)
編輯:郭成